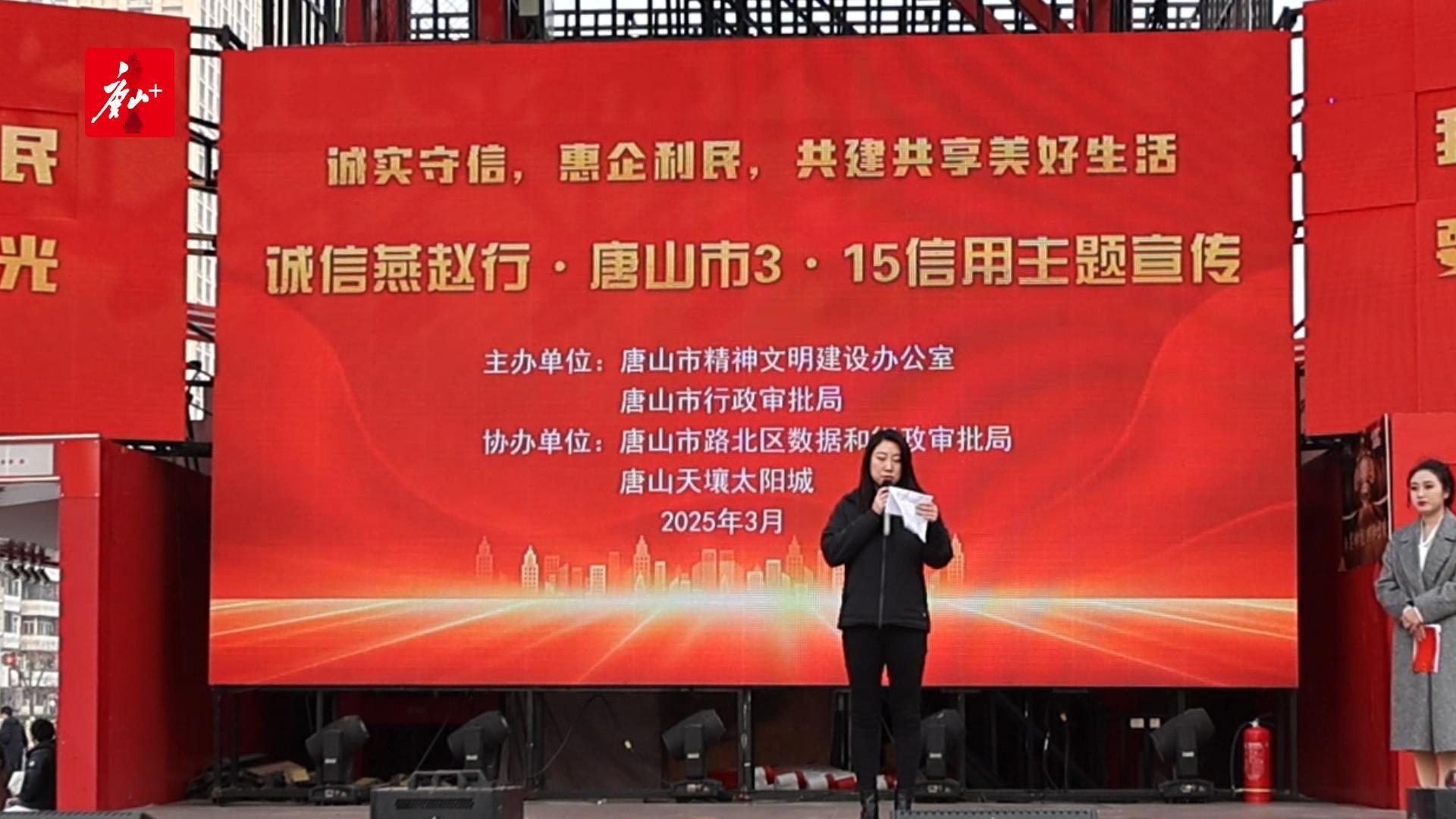从刚记事起,我就知道父亲有一块手表,黑色的表盘上缀有荧光点。我多次趁着月色,偷偷拿到院子里观看那神秘的幽幽绿光。母亲生前讲过,父亲在英国人统治开滦煤矿时期被提为中级员司,为与之身份匹配,咬牙买下了这块手表和一辆老掉牙的德国产自行车。自行车用于上下班,手表则为回农村老家计时。父亲对这块手表爱不释手,几乎从不让它离身。那时我们兄弟姐妹,无论上学还是赶集,他都指着手表督促我们守时守点。
这种精准的时间观念对我影响至深,我和父亲一样,在几十年的职场生涯中,从来未因误时而误事。而我妻子恰与之截然相反,几次出差因误时而误车。父亲只能无可奈何地慨叹:“人家火车不等你呀。”自然,这也是我们夫妻间吵架拌嘴的原因之一。
1964年我参加高考,父亲破例把那只手表摘给我,让我在考场上把握和控制时间。有了它的护佑,我临场发挥异常顺利,如愿考取了心仪的军校。父亲大喜过望,本想就此将他的心爱之物馈赠与我,但遭到母亲的断然拒绝,理由是在我们这个贫寒之家,当年那表、那车和一台缝纫机,的确是全家的最贵重之物,父亲的做法显然顾此失彼。
军校的生活紧张而多彩,作为学员的我们佩戴着大沿帽、肩章列队出行,军歌嘹亮,口号阵阵,立即成为街上的一道风景,引来众人的围观和小孩子们的嬉闹:“解放军叔叔好,穿皮鞋,带手表!”穿皮鞋并无手表的我,可能就是从那时起悄悄萌生了买表的愿望,并为此开始从每月几元的津贴中攒下一小部分准备买一块属于自己的手表。
两年后,我手头上有了60多元的积蓄。大串联开始后,我和千百万学子一样穿行于天南地北之间。那年母亲似乎为弥补父亲的亏欠,主动资助我30元,要我在串联途中买块手表。其实许多学员已成了有表一族,我也刻意留心各地商店的柜台(那时手表并不好买)。记得是在辽宁旅顺,和我一道出行的钱云山同学首先发现了一家商店有表在售,我当机立断买下了那价值80元的上海半钢手表。自此我平生第一次拥有了手表,它陪伴我远赴东北边陲,在北国的寒风雪夜中站岗放哨。
我复员回地方后在工厂挥汗如雨,在课堂上传道授业,在表针的滴答声中送走了十几个春秋,它一直忠实地陪伴着我,直至在唐山大地震中失落。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紧缺经济的条件下购买三大件是需要票证的。我所在的唐山教育局办公室虽然直接掌管着票证的分配权力,但下属十几所学校,粥少僧多,同事们都自觉自愿从不染指那些票证。恢复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状态的我,还两次谢绝了领导的照顾,把到手的表票主动退回。办公室副主任张敏大姐,这位从战争的硝烟中走来的老同志,见我因无手表而耽误了接上幼儿园的女儿,还是牵挂于心。后来,她从老伴所在部队搞来几只南京试销的钟山牌手表,于是,我的腕上才有了平生第二块手表。
改革开放带来的商品经济繁荣,早已使手表这种寻常之物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只钟山牌手表转送母亲后,我又带过多少手表呢,全钢手表、全自动表,电子表早已是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数字符号。
那天我无意中翻到一只杂物盒,里面竟躺着十几块手表,其中既有当年价格不菲的西铁城,也不乏有在广州受骗淘来的水货和伪劣品。睹物思及过往,颇有一番感慨在心头。如今,它们连同与之相伴的故事,均悄无声息地沉睡在那个无人问津的杂物盒里,慢慢被忘却了。天道有轮回,现在我又重回几十年前无表的原点了,那是因为有了手机,我再也不需要它了。(张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