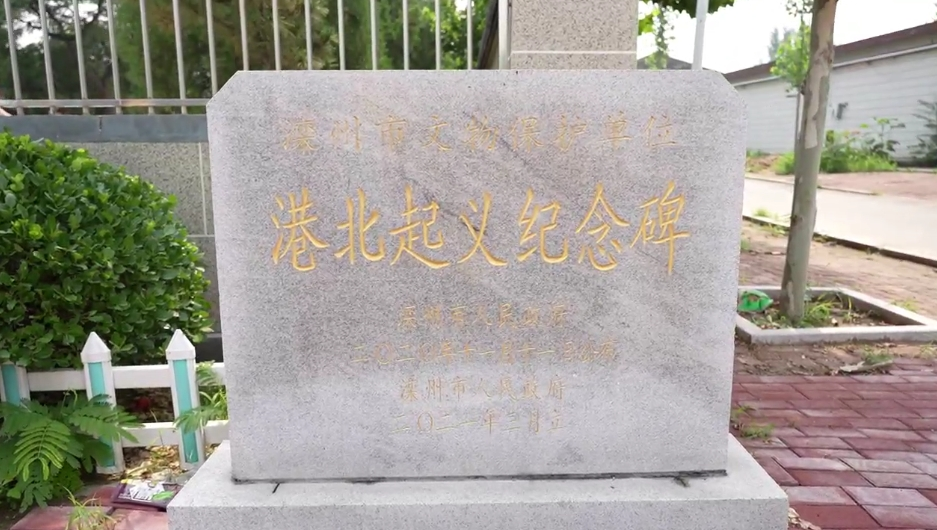我爷爷那一辈兄弟三人,大爷爷家有五个姑娘,二爷爷家有三个姑娘,我爷爷排行老三,有三个姑娘、两个儿子。哥三个居住在一个大套院里。二爷爷去世早,我没见过面,秀华二姑是我二爷爷家的二姑娘。据说二爷长得极好,又能干,靠着勤劳智慧,积攒下一份很好的家业,可惜没有男丁接续,只好让最能干的二姑招赘女婿,继承了家业。
我爸常说,你二姑是个苦命人。其实,秀华二姑更是个有故事的人,她的人生也是部分乡村人生活的缩影,如果你在乡村生活过,也可能碰到像我二姑这样的人。
一
在我们的大套院里,二姑继承的家业算得上殷实。她家有一座正房,后院有东西厢房,前院也很大,菜园、井窖、鸡舍、猪圈一应俱全,还有一个好看的门楼。我特别记得正房的东屋里,挂着一排镜子,里面镶着古典美人照,现在仔细回想,应该是唐代美人,高高的发髻,艳艳的红唇,樱桃小口一点点,主基调是典雅的蓝色,一直挂了很多年,直到地震后才不见了。
小时候,我很喜欢在她家玩,主要是因为她家前院里有一个宽大的石台,在上面躺着看天特别舒服,还能在上面玩抓骨头。夏天傍晚的时候,因为等着在大石台上玩,所以,经常看她们一家人在那里吃饭,每个人端着粗瓷大海碗,吃稀里咣当的疙瘩汤,这一幕在我脑海里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个大石台除了宽大,也应该很有些年头了。石面并不是如镜般的光滑,而是有许多麻坑,但凸起的部分光润明亮,不知经历了多少年轮,也不知多少人抚摸过它,触手温润的包浆就是证明。
大石台旁边就是一个菜园,二姑爱种葫芦。夏天,有月光的夜晚,躺在温热的大石台上,看着天上清澈妩媚的月亮,看着月光下摇曳的、雪白的葫芦花,激发了我年少时的想象,我把它想象成月亮花。后来还因此写过一篇散文《月亮花 葫芦梦》,刊登在《儿童文学》杂志上。
二
要说二姑命苦,可能与招赘的女婿有关。二姑夫长得矮小精瘦,且当过国民党的兵,似乎又跟老家失去了联系,据说是热河那边的人。在那个时代,二姑父这样的身份自然是不被待见的。所以,从我记事起,她家里都是二姑的笑骂声,二姑父总是无声无息的,很少见他说话,好像他也不大在家里住,总是在村东松山的小房子里看果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存在感特别低,仿佛是可有可无的人。
他与二姑生了几个孩子,也就是我的三个表兄和一个表姐,这应该是他带给这个家最大的价值。在这种境况之下,这个家主要靠二姑挑起来。
二爷真是选对了人,秀华二姑的能干、会过日子可是远近闻名。家里地里一把抓,没有二姑干不了的活儿,而且活到老干到老,记得二姑快七十岁时还放养着一群羊。
二姑爱骂人也是出了名的。她高门大嗓,那种特别难听的“乡骂”时刻挂在嘴边,不论好事坏事,在她嘴里都是通过“骂”来表达。因为二姑爱骂人,我总是绕着她走,尽量不进入她的视野,也特别庆幸自己的爸妈有文化、不骂人。
但现在回想起来,我有些理解了二姑,觉得二姑的“骂”是来撑场面的。因为她招赘了女婿,属于外姓人家,二姑夫又撑不起门面,骂人是二姑的一种自我防护。她必须把自己武装成刺猬,有一些锋芒,看起来不好惹,才能抵挡一些可能遭遇的伤害,给家里罩上一层虽不好看但实用的保护伞。后来习惯成自然,即便表扬你也是通过某种“骂”来表达,骂人成了她支撑生活的一种技能。
三
眼看着几位表兄都长大成人,很快到了娶媳妇的年龄。而这样的家庭环境,很显然不被当地人看好。二姑太难了,没办法,只好拼命积攒家业。但是不能偷不能抢,在那个年代,也不可能做些小买卖赚钱,唯一的途径就是口里夺粮。
二姑家的饭食实在是太差了,能省则省,以至于表兄们的名字都冠之以“省”,大省,二省……省,成为她家生活的常态和准则,经常吃难以下咽的白薯面疙瘩汤。记得,二表兄曾经气愤地罢饭,嚷嚷着:“这是啥饭啊,不吃了,不吃了!”二姑眼一斜,恶狠狠地说:“不吃不饿!”其实,二姑何尝不想吃饱饭,吃好饭,她也是没办法呀!不这样省,西厢房那几缸麦子、谷子、高粱从哪里来呢?那几块时兴的条绒布料哪里来?
每次有来相亲的人,相完亲,下一个程序就是相家,二姑都无一例外地打开她家的西厢房,让人们看她积存的几缸粮食和布料。我们小孩子也乘机钻进去,跟着兴奋地观赏一遍,心中总是暗暗称奇,这金子一般的粮食和布料啊!也只有这一刻,二姑的脸上是带着笑的,有着一丝难得的骄傲。
后来,二姑如愿以偿,从迁西给两个儿子娶了漂亮的媳妇。为什么从迁西娶媳妇呢?因为那时候,身处大山里的迁西非常穷困,姑娘们都希望走出大山。嫁到我们这里,对她们来说是一种上乘的选择。当然,娶迁西姑娘要多拿彩礼,二姑拿得出来,只要能娶个好媳妇就行。而如今,美如画的迁西,早已成了宝地,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到三儿子该娶亲的时候,已是八十年代,家家日子都好起来,也就顺理成章地娶了当地的媳妇。彼时,二姑依靠自己艰难打拼,终于完成了她的人生大业,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很快,二姑有了孙子孙女,她每天抱着孙儿东家串西家走,喜气洋洋,本就高门大嗓的她,此时声音更加响亮,整个大套院都回荡着她的笑骂声,想来,那是二姑一生中的高光时刻。
那时候,因为我大哥身体不太好,也到了娶媳妇发愁的时候,二姑常常抱着她的小孙子来我家串门,还不忘汇报谁家儿子结婚了之类。二姑走后,我妈叹口气说:“看看,你二姑又让咱们‘眼气’呢。”
我这里并没有贬损二姑的意思,她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于实现,需要炫耀一下,释放一下多年来积郁的情绪,我现在特别能理解她。其实,二姑是特别有“家里外头”观念的人,如果我家遇到什么险境,以二姑的脾性,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冲上来,保护我们。
在乡村这个熟人社会中,人们相处既简单又复杂,人们有利益之下的市侩与狡诈,也有当你遭难时护你周全的善良和热情。这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世界,人性也是多样性的,摇摆在灰色地带也是一种选择,不过是一念之间,这才有了多姿多彩的人类社会和戏剧人生。
四
可是,这样的好光景维持了没几年。
先是大表兄出了意外。年轻人喝酒逞强难免醉酒。大表兄在一次醉酒之后,被放在烧得滚热的炕上睡觉,还盖了被子。谁都没料到,这样的一个无心的、也是没有常识的处置方式,却生生要了一个年轻人的命。大表兄长得好,可能随了我二爷,一直是二姑的骄傲,没想到,竟然遇此大难,家也就随之散了。
这样的打击几乎要了二姑半条命。
紧接着,二表兄也出事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春风吹到了乡村。一些有想法的、不安于现状的人也开始行动起来。二表兄就是其中之一。他到处找关系,交朋友,拉买卖,想方设法地挣钱。但那个时候,市场不规范,仿佛处处是机会,又到处是陷阱。不知怎的,二表兄被人追命似的追债,走投无路的他,终于在一位老乡的帮助下,逃离了家乡,从此再没回来。开始几年杳无音信,后来和家里联系上,说是在成都。再后来,又让一家老小去了成都,而自己一直没露面,即便那年二姑去世,都没回来。二表兄极好面子,看来不到衣锦还乡的程度,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消失的二表兄让二姑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悲伤,她曾经高昂着的头、梗着的脖子似乎软了下来。晚年的时候,不知谁的引领,二姑忽然决心要说好话,做好事,再不骂人。那段时间回老家看我爸妈,我总是关注二姑的动态。常问我妈:“二姑还骂人吗?”我妈说:“不骂人了,你二姑还真是说到做到。”
难道二姑对自己的人生做了反思,把自己命运中遇到沟沟坎坎归结为骂人了?极有可能。人到晚年,有更多的时间反思,她一定是找到了别在自己命运里的楔子,并勇敢地开始自我救赎,不论以什么方式,都是极难得的。唉,我可怜的二姑!
五
二姑倒是没骂过我,顶多一句:“你个小丫头片子。”
那些年我考学备受煎熬,一年又一年,被乡里人嘲讽。二姑见了我妈,也说:“小丫头,念啥书,不念书就不能活了?你看我家文霞,这几天又给我拾了一垛柴禾。”
每当二姑这样说的时候,我就特别生气,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我就是要念书,一定要考上大学。现在我知道,二姑的这句话里,一半是心疼,一半也是对女孩的轻视。二姑是老观念,喜欢儿子,对唯一的闺女也不待见。文霞表姐出嫁前,天天干不完的活,还挨着二姑的各种骂。可是到后来,大儿子没了,二儿子远走他乡,是这个唯一的闺女撑起了二姑的晚年生活。
那时候,我回老家,常常遇见文霞表姐回来。每次来都买好多肉菜,吃的穿的从来不空手,二姑的晚年生活全仗着表姐打理,表姐也给了她心理上的依靠。
我妈常说:“别看你二姑过去看不上文霞,现在这个闺女可‘得济’了。”
后来,二姑也不得不承认,有个闺女真好。
六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对这些老辈的亲人是满满的疼惜,他们吃了太多苦,二姑劳碌辛苦的一生尤其让人心疼。老辈的女人啊,一生陀螺似的围着别人转,从来没有自己。她们全部的人生意义是把上一辈积攒的家业接下来,让自己的后辈成家立业,过上该过的日子。而自己的那一点点快乐,都是活着的一点附加值。
人生如海,我的文字记录算是一种人生故事的打捞,记录一个时代、一群人曾经的生存状态。乡村的女人是一群被忽略、被遮蔽、被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的人。她们的过往早已无声无息,如同石缝中艰难生存的植物,一生充满挣扎,勤劳、隐忍、顽强地过完自己的一生,所有的波澜只是她们内心的风景。
我写这些文字也是一种比照。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没有人是孤立的,我和奶奶、二姑们有过共同生活的时光,我们的影子曾经如光如弦交织在一起,弹奏着或喜或悲的歌。
她们的生存状态触动了我,让我不甘于走她们的老路,决意要闯出来,开启自己的另一个世界。她们的人生故事也是对现今生活的一种参照,比照老一辈人的生活,我对现在的生活充满感恩。
人生百态,苦辣酸甜。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独特的,即便如一棵小草般平凡的生命,也都值得尊重。
我那个泼辣、爽快、干练、热情的二姑啊,你在人世间受尽磨难和煎熬,但愿在另一个世界平和安逸,不再受苦。
是不是没想到我写了你的故事?我仿佛听到你在笑骂我:“你个小丫头片子!”
(刘君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