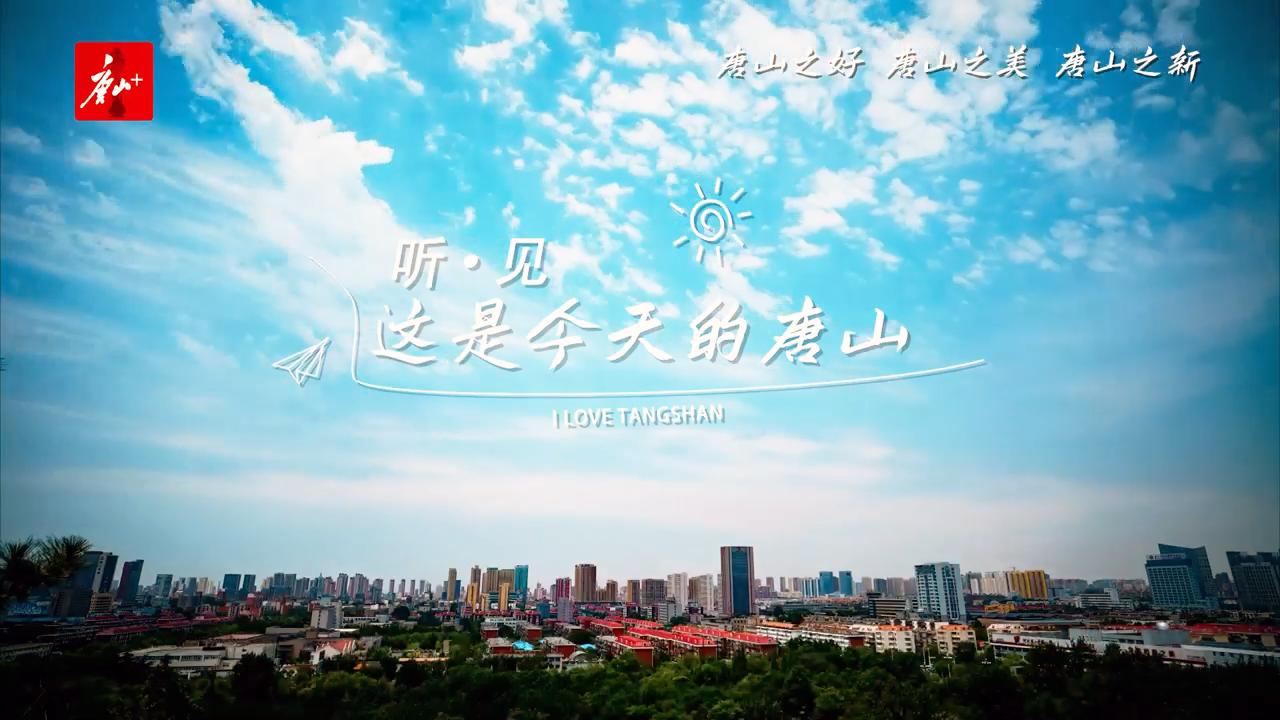华北平原的夏天,日头像被火炉煨过的铁饼,贴着庄稼地往下烙。白凤桃成熟那阵子,村里老人总说:“桃儿是吸着地脉的凉气长的。”这话倒不假,白凤桃树爱往深处根扎,偏要挑那些背阴的坡地,树根好似能探到地下水脉,结出的果子才水灵。
当时村东头有片集体的桃林,包产到户分给了张、李两家合伙经营。白凤桃树生得娇气,不像麦子玉米能抗旱,非得喝饱地下水才肯挂果。春天时满树盛开桃花,那粉红色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是大自然最精致的艺术品。等花谢了,青桃儿便藏在叶丛里,像偷吃蜜糖被逮住的孩子,不敢探出头。
这桃儿金贵,村里人舍不得用化肥。开春时,老桃树底下总堆着腐熟的羊粪蛋子,村民再把羊粪混合着草灰撒在树根处。羊粪是活性的,不像化肥烧根,能养出甜里带香的桃味。六月底七月初,桃儿开始泛红,树梢上最先熟的果子总要被麻雀啄几个洞。这时候孩子就成了护桃员,他们举着竹竿满林子撵鸟,倒像是跟天上的飞禽抢食吃。
挑白凤桃有讲究。外行人总爱挑红透的,其实顶好的桃儿是“半脸红”——朝南那面晒成胭脂色,背阴面还泛着青白,这样的桃儿糖分积得足,咬开能见蜜汁。村里的老人最会挑桃,他们总说:“桃儿跟闺女似的,太俊俏的未必中用。”他们挑桃时总要摸一摸,手指按在桃屁股上,若能按出个小坑又迅速弹回来,这桃儿准保脆甜。
那年我十二岁,头回跟着父亲去桃林收桃。天还没亮透,父亲就扛着竹筐进了林子。晨露沾在桃叶上,亮晶晶的像撒了把碎银子。父亲摘桃时总要戴副白手套,说是怕手上的汗气腌了桃皮。摘下的桃儿不能乱放,得轻轻码进铺着麦秸的竹筐里,一层桃儿一层麦秸,像是给桃子盖了层棉被。
日头爬到树杈时,竹筐里的桃已经堆成小山。父亲把扁担往肩上一扛,筐子随着脚步吱呀晃动,桃儿在麦秸里挤挤挨挨,倒像是挤在炕头上说悄悄话的娃娃。镇上的收购车要晌午才到,这会儿的桃儿还带着地气,得赶紧找个凉快地儿镇着。
井水就是天然的冰窖。院里那口老井,井壁青砖缝里长着绿苔,水深得能照见人影。父亲把水桶拴在井绳上,我蹲在井沿数着绳结——一、二、三……数到十七个结,水桶就扑通一声落了水。打水是门技术活,摇辘轳要匀着劲儿,太急容易把水桶晃翻,太慢又打不满。父亲总说:“井水是活水,得顺着它的脾气来。”
装桃的水桶要另备。父亲把新摘的桃儿轻轻放进水桶,用井水没过半桶,再拿块木板压在桃上,怕有调皮的桃儿浮上来。等桃儿在井水里泡上两个钟头,切开时能看见桃核周围凝着层霜碴,咬一口,脆生生,甜津津,汁水顺着指缝往下淌,连手背上的汗毛都沾了蜜。
最馋人的要数“井桃宴”。日头最毒的时候,把井水镇过的桃儿端上桌,桃皮上凝着细密的水珠,像是刚洗过冷水澡的娃娃。父亲用菜刀沿着桃缝一转,桃儿就咔地裂成两半,露出琥珀色的桃核。我捧着桃儿蹲在门槛上,桃汁滴在青石板上,引得蚂蚁排着队来舔。
那年白凤桃丰收,父亲破天荒留了两筐在井里镇着。夜里起风时,我听见井辘轳吱呀响,偷偷爬起来看,见父亲正把水桶往上提。月光照在桃皮上,泛着珍珠似的光。父亲把桃儿码在竹匾里,说是要给大姑送去。我舔着嘴唇问:“不甜怎么办?”父亲笑着掰开桃儿递给我:“尝尝不就知道了?”
如今超市里的桃子裹着保鲜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再甜的桃儿也比不上井水镇过的白凤桃。那年夏天,井沿上的水珠,竹匾里的月光,还有父亲手上的桃香,都随着井水渗进了地底,成了最清凉的记忆。
(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