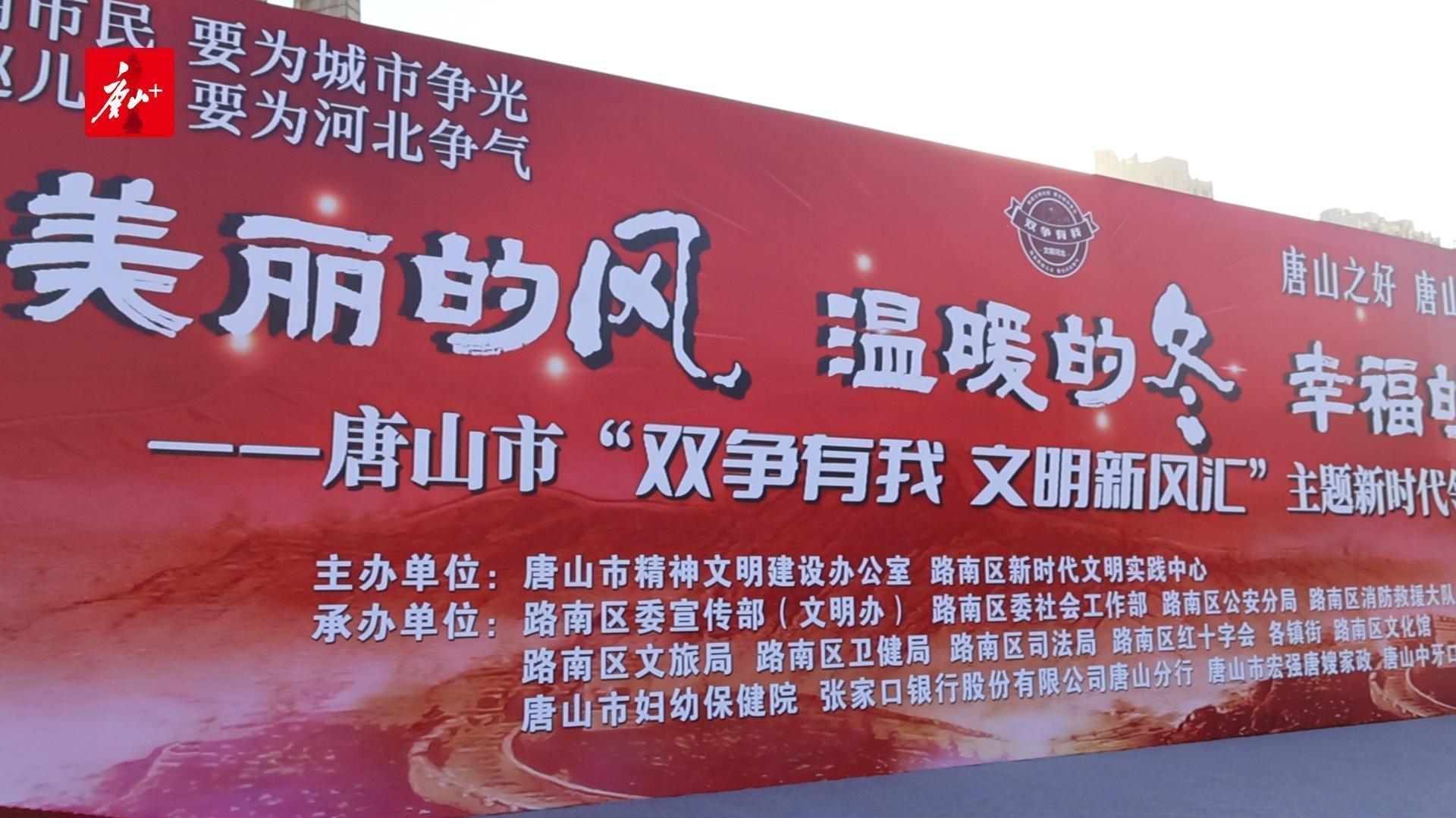我小的时候做过一次踩花大盗。对,不是采花的采,而是踩踏的踩。
那应该是一个初夏的中午,我们几个小朋友背着小书包结伴而行去上学。尽管我在之后多年都不曾找寻到那条路,但是记忆中绝对有那样一条偪仄又安静的小巷。打开的一扇扇木质窗子上涂着褪了色的油漆,而这些窗子就静默在夏日午间的宁静与闷热之中。我们在几扇窗下发现一垄刚发芽不久的花。不知道是谁起的头,一边走一边用脚往花苗上用力去跺,大家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一般,争先恐后去重复这个动作,花苗则在东倒西歪的毁灭之中满足了几个淘气孩子彼时扭曲的快乐感官。
终于,嬉笑声惊动了主人,我们被全体捉拿归案。那是一个阴凉昏暗的屋子,我们怔怔地站了一地。一顿严厉的批评过后又不知是谁起了头开始哭,我们便又一窝蜂地哭泣起来。哭声惊醒了午睡的小孩子,他们纷纷睡眼惺忪地前来指责我们:“谁让你们来这哭的?把我们都闹醒了!你们也太讨厌了……”我一边流下悔恨的泪水一边在幼小的认知系统里推断出这是一个工房区里的托儿所。我甚至完全忘了大人们是怎么教训我们这群可恶的小孩,只清晰地记得自尊像一层薄薄的糯米纸,怎样被那些更小的小孩儿的口水一句句戳破。其实我们也还只是学龄前儿童,是学校里育红班中的小学生“预备役”,比他们大不上一两岁,但被更小的孩子无情地数落让我简直感到尴尬窘迫的成分胜于做错事的悔恨。那次为数不多的被抓现行即便过去几十年,仍清晰又朦胧地残存在记忆里。
就是这样一个童年里的踩花大盗,成年以后变成了一个极爱植物的人。有人说对一朵花的喜欢就是把它采摘下来据为己有,对于一朵花的热爱就是给它浇水施肥替它遮风避雨,让它活得更加绚丽茁壮。从前我真是一个路边一朵蒲公英也要掐来别在衣襟的人,后来渐渐明白,为了短暂的悦己而提前结束它本该更长久的花期其实只是爱花的最低级阶段。今年在塞罕坝的草原上,我再次见到翠雀花那夺人心魄的一抹抹蓝色,再次见到仙气十足的蓝盆子花的可爱身影,我只是流连着用手机和眼睛记录下它们的美好,没有动手采摘下一枝。那其实是从前乐此不疲的事,续集也都无一例外地发展为无奈地看它们迅速萎谢在手中,扔也不是,留也不是。我终不再觉得那是有趣的事,索性做个袖手旁观的赏花人。
年轻时看过一部电影,一个学校把所有的参天大树都伐倒了,老校长对此捶胸顿足。那时我们都极为不解,砍树与教书育人有何瓜葛,他为何会有着如此强烈的愤懑。多年以后,我们恍然想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话,对老校长口中所念“种有种的理由,砍也有砍的无奈”有了些许似懂非懂的解读。
说到砍树,这几日在家养病,见证了楼下伐木的全程。一棵棵高大的玉兰和果树顷刻之间被斩首示众。我躺在床板上听着电锯嗡嗡的嘶吼,仿佛那锯片也一同切割在我的心脏之上。那春天一树树或粉或白的玉兰,秋天一枚枚火红的柿子,一地玲珑可爱的枣子,还有四季常在的鸟语啁啾,都伴随着一声声巨响,轰然倒塌,一去不复返了。我动用知之甚少的法律常识竭力用沙哑苍白的嗓音与砍树负责人狠狠地吵了一架。但是那些齐着地皮的树桩就像菜市口无辜良民的躯干,已然人头落地,无力回天。回想站在树下仰望高大树冠的那些美好时刻,春的繁花一树,秋的硕果累累,内心久久无法平静。我不禁想起那句“种有种的理由,砍也有砍的无奈”,却依旧难以释怀。
人生过半,我不再是那个以踩花为乐的孩童,不再是那个以摘花为美的女子,亦不再是对砍伐树木无动于衷的中年人。我能做些什么呢?我什么都不能做。其实我也不过是一只深陷藩篱不能自赎的驴子。
(拉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