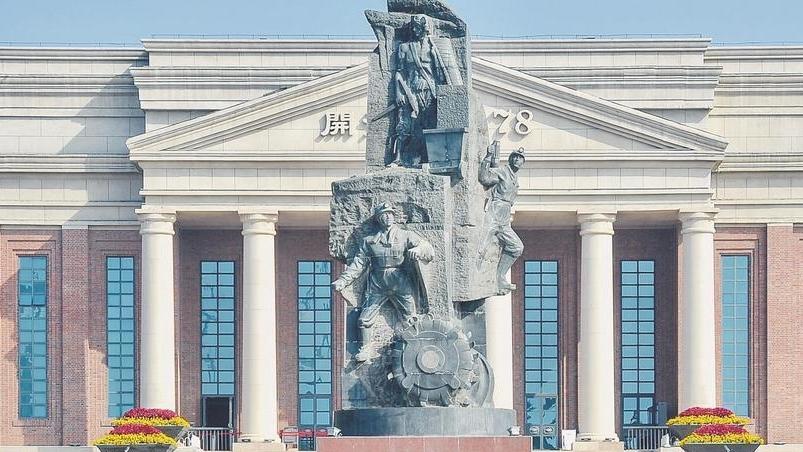争妍占早,只有梅同调
妙玉大概是《红楼梦》里最高冷的女子,她的出场总是自带一种清冷。也难怪,她虽出身官宦贵族家庭,奈何早早入了空门,与红尘无缘了。
妙玉也并非心甘情愿皈依佛门的,而是因为自幼体弱多病,买了许多替身都不中用,这才无奈带发修行的。妙玉的身份因此非常微妙:她既带发修行,是佛门弟子,又有无数家传珍宝傍身,有丫头、婆子在身边服侍。贾府建成了大观园,王夫人亲自下了帖子将她请到家庙陇翠庵。陇翠庵,从此成了妙玉的落脚处。
刘姥姥二进荣国府,贾母带刘姥姥游园,曾来到陇翠庵喝茶;宝玉与姊妹联诗落了第,也曾被李纨罚去陇翠庵向妙玉乞一枝红梅来赏玩。妙玉与她的陇翠庵,因沾染了茶香与梅香而格外馥郁。若用梅花比妙玉,未尝不可,只是终究少了些韵味,毕竟那支梅花签已将“霜晓寒姿”的美誉给了李纨。那么,妙玉像什么花呢?
我想,不如就将妙玉比作一朵瑞香花吧,似乎比梅花更贴切。

仙品只今推第一
瑞香是中国传统名花,四季常绿,因花香浓郁而得名“瑞香”。瑞香花株形挺拔,叶色俱美,被誉为“上品花卉”。至于它被引入佛教,还有一个古老的故事:传说庐山有位僧人昼寝于磐石之上,睡梦中被浓香熏醒,后寻到花株,就将其命名为“睡香”。又由于这花在严寒的春节前后盛开,人们以为祥瑞,便改称“瑞香”。瑞香的花期,正值群芳消歇之际,其花香极其浓烈,因此又被人称之为“夺香花”。
“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作者这样热烈地赞美妙玉。她有兰花般的气质,又有谪仙般的才华,怪不得作者称她“可怜金玉质”。整部《红楼梦》,论仙气飘飘,能和“神仙似的”的林妹妹比肩的,似乎只有妙玉一人。就连黛玉,也曾因不懂茶道而被妙玉嗤笑呢!
世人总是觉得黛玉小性儿,却从来无视黛玉的宽容友善:被妙玉当面讥为“大俗人”,也并不与她相争。黛玉不争的背后,是深深的理解与懂得,是对同样出色的妙玉的惺惺相惜。
清香元不是人间
书中说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与黛玉相比,妙玉的“天生成孤僻人皆罕”怕是有过之无不及了。
瑞香花在宋代曾备受追捧,与牡丹、兰花、蜡梅等平起平坐。可是明清以来,却因其香味过于浓烈,与文人对“淡雅”的要求相悖,渐渐不合时宜,开始被冷落了。更有甚者,将其比作花中小人,编造出瑞香花的香气对其他的花有害的谬论。这与妙玉的“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如出一辙,妙玉之孤就像瑞香花的香气一般,受到世俗的排挤。且不说那些俗人,就连性情平和、素有“大菩萨”之称的李纨都对妙玉颇有微词。芦雪庵赏雪联诗,宝玉落第被罚去向妙玉乞红梅,李纨亲口对众姊妹们说,“可厌妙玉为人,我不理他”。
妙玉之“可厌”,究竟是“可厌”在何处?李纨一向与人为善,为何对妙玉如此反感?作者并没有明说。李纨是贾府孀居的节妇,她清净守节,为人亦宽厚善良,深得贾府上下的爱重。“洁”是李纨作为一个寡妇的道德底色,她不问世事,心如止水,只管课子读书,陪伴小姑。这样安分守己、不事张扬的一个人,某种程度上与妙玉相似:她们都远离红尘的喧嚣熙攘,可是为何李纨会讨厌妙玉呢?
我想,大概是因为在李纨的价值体系里,实在看不惯妙玉那样的言谈举止。妙玉在旧交邢岫烟的口中是“女不女,男不男,僧不僧,俗不俗”的“放诞诡僻”之人;宝玉也深知她“为人孤僻,不合时宜,万人不入他目”。可是岫烟与妙玉相交多年,再度相遇,是难得的贫贱之交;宝玉对每一个生命个体都不乏尊重与欣赏,因此他们都能或多或少地体谅妙玉。而李纨自幼家教甚严,她的人生谨遵封建社会的信条,不越雷池半步,她的眼里,自然容不下妙玉。
侵雪开花花不侵
妙玉虽身入佛门,心却还在红尘,她不甘于过李纨那样槁木死灰的生活,而是执着于世间的一切美好。
中秋之夜,她偶遇联句的黛玉、湘云,便邀请二人进去喝茶,还为二人将诗巧妙结尾。三个貌美才高的女孩子,成为那年中秋之夜里一道曼妙的风景,谁会刻意记住妙玉是个带发修行的尼姑?她分明先是个灵动美丽的少女!不但读者,便是妙玉本人,当时亦以闺阁女子自称,声称作诗不可“失了咱们的闺阁面目”。
妙玉虽人在佛门,心却无处放置。
“僧不僧,俗不俗”的评价其实也是妙玉纠结、摇摆之处。妙玉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妙龄少女,她原本应该像贾府千金那样待字闺中,可是命运却将她推入了空门。人说一入侯门似海深,佛门何尝不深呢?佛法里的万念皆空,妙玉做不到,她从来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她不过是个命运多舛的少女。这滚滚红尘中还有她太多的留恋与不舍,这些不舍注定了妙玉无法真正成为一个佛家弟子;同时,这万丈红尘又有太多的肮脏违心愿,又使她意难平。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在摇摆不定,她还太年轻,在与命运的拉扯中,她并没有习得佛教的真谛,更无法获得心灵的自在与解脱。她矛盾、挣扎,自己与自己尚且无法和解,又如何习得众生平等与慈悲为怀呢?
因此,她可以将自己的五彩官窑小盖钟给贾母献茶用,也肯用“老君眉”来迎合贾母的喜好,却无法接受刘姥姥用她这个杯子喝了茶,洗茶杯的时候单独将这茶具撂出去。她甚至不如宝玉宽厚仁慈,宝玉尚且有一颗怜老惜贫的心,她却对穷苦的乡野老妪满心嫌弃,不见一丝怜惜。
她枯燥乏味的生活中,亦有少女的情思。她请钗黛喝体己茶,口口声声将宝玉排除在外,却把自己日常使用的杯子给宝玉用,这一细节使她备受诟病。是啊,刘姥姥用过的杯子她嫌脏,直接不要了,她自己的绿玉斗却给个男子用,着实惹人非议。可是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愿也不能将妙玉污名化,我宁愿相信,妙玉作为一个少女的纯净与自尊。宝玉不同于浊世须眉,与他的思想相比,他如宝似玉的外表反倒是不算什么了。宝玉体贴女子,呵护女子,他对妙玉的懂得使他可以成为妙玉的知己,既然如此,妙玉视他为自己人最自然不过的了。
“侵雪开花花不侵,开时色浅未开深”。琉璃世界的白雪红梅,傲立于陇翠庵中,花吐胭脂,香欺兰蕙。妙玉有梅的风骨,但是与红梅的艳丽又不同,妙玉身上更多的是冷傲。开在陇翠庵的红梅还会被宝玉讨了去插瓶供大家观赏,而妙玉却是那样孤独,被迫远离了尘世繁华,像极了自开自落的瑞香花。
惆怅音尘难再会
妙玉的判词让人意难平:“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
妙玉最终不知道陷入了怎样的淖泥中?《红楼梦》未完,妙玉最终的命运不得而知。可是她的判词与曲子都暗示了这个仙女一样高洁的女子与诸钗一样不得善终。甚至有人根据“风尘肮脏”推测妙玉堕入了风尘,流落烟花巷,对于这种说法,尽管觉得残酷至极,又无可辩驳。后四十回的续书中,妙玉被强盗迷晕抢走,最终不知所终,与前者相比,这种结局并不能使人稍微欣慰一点。而作为一个读者,除了扼腕叹息,我们又能怎样?
命运全然不讲理,妙玉总是让我想起黛玉和香菱。
巧得很,这三个女子都是姑苏人。黛玉自述从会吃饭起便吃药,癞头和尚要化她出家去未果,断言她若要病好,不能见父母家人之外的人,又不许见哭声。而香菱在甄士隐怀中时被和尚索要,直指其为“有命无运、累及父母”之物。黛玉与香菱没有出家,妙玉带发修行,可是殊途同归,她们都未曾逃过命运的捉弄。
黛玉泪尽而逝,香菱香魂归返,她们如花般美好,也如花般脆弱。“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无法否认,如无瑕美玉般的妙玉终究陷落污泥,在污浊的人间挣扎,亦如同一朵瑞香花,败落了。
(杜海红)